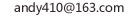The Summer is Gone——八月,是七月流火(电影《八月》影评)
更新日期:2024.06.01
说实话,电影开场我是有些失望的。并不好看的演员,枯燥乏味的家常对话,我一直抱着把这部片子当文艺片来看的心态,除了黑白的画质和剧中老旧的楼房,似乎没有感染人的艺术气息。
但“八月”二字出现的时候,电影的英文翻译便给了我一个极大的震撼,The summer is gone,不是简单直接的August,而是婉转的表达——夏天走了。那一刻我意识到它可能是跟我往常所看的文艺片是不一样的,并不只适用于无聊的消遣,于是决定认真观摩解读,好好写一篇影评。
故事背景是在九十年代初的西部小城,国家开始实施国企改革,铁饭碗被打破,国有制片厂家属院里,每一个简单家庭的生活都被改革所影响,而十一岁的小雷就这样在经济变革与家庭改变之间懵懂成长。电影里每一个人物都有鲜明的个性,都是一个时代的体现,比如小雷,比如父母和一群亲戚,比如看似无关紧要的地痞三哥。
虽说这是一部致敬父辈的电影,但几十年来,许多景象还是日复一日从未变过。大爷大妈们在嘈杂的环境下打牌,四周不乏一些围观的人,小孩儿穿着廉价的衣服凉鞋在旁边跳橡皮筋,大人喊小孩儿回家吃晚饭时男孩一脸不情愿的说“我想多玩会儿”。小雷的童年也是我的童年,准确的说,是我小时候生活在乡下时眼里看到的童年,不是经历的童年。我充斥在弹琴画画练字背单词中的童年并不快乐。
也许是喜欢孩子的缘故,一直觉得孔维一——就是剧中的张小雷小朋友,他笑起来真好看,当他看着妈妈用古怪的方式浇花,“噗嗤”一声就笑了,那是小孩子才有的调皮捣蛋古灵精怪的笑,连带着看电影的我都发自内心的笑了。许多人围在河边看三哥在羊肚子里取出菩提子(并不确定三哥是在干什么,凭直觉所想),一群大人里面,只有小雷的眼神带着孩子才有的好奇、探究。大人都是沉闷死气的,只有孩子为生活的枯燥带来了生机。
家属院里运动会拔河,还未分出胜负时,厂子里的车动不了了,大家都去推车,直到车子都发动了许多人还是跟着跑,大喇叭里念着热血沸腾的诗仿佛这是一场闹剧。随着人群渐远,镜头聚焦到小雷身上,小雷的神情一半茫然一半似乎又懂得了些什么,半知半解的眼神,瘦瘦小小的身影,这样孩子气对未知的不解,总让人想越过面前的屏幕去抱一抱他。小雷挥动着手里的双截棍,咚咚响的跑到楼上尽头的房间,偷偷的打开门,又忍不住问“爸爸,这是什么?”“放电影。”“你为什么不去参加运动会?”爸爸当然不会回答,跟小孩子怎么解释得清楚,再说就算回答,又能回答出什么。他剪了一截胶片给小雷,孩子终归是孩子,马上拿到窗边把玩,问父亲“这是谁呀?”“这是你老云叔叔。”这一刻父子俩的场面格外温馨,窗外通过胶片透进来的光,仿佛是父子俩的希望。
父亲张晨一直像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不要低下高贵的头颅”——这恐怕是不需要考虑生存的艰难不识愁滋味的少年才有资格说出的话,冲动的意气用事的父亲,喝醉酒的父亲,不愿向现实妥协的父亲,带小雷看电影时流泪的父亲,多像个文艺莽撞的大孩子。不要说是一个父亲的年龄,就连现在的我们,逐渐成长麻木,操劳担心过不去的现在和未来,已然很少在别人的故事里流自己的泪了。
电影中场,小雷开始由小孩转变为少年了。学校主任一回头看到小雷,“这谁家的小孩儿?”“咋呀”——少年身上独有的戾气。还有后来父亲与小雷没有看成的那场电影,有钱人的倨傲和他儿子胖小子眼里的轻蔑,瘦弱的小雷脸上再也藏不住愤怒,他的手和身体已经做出了最直接的反应。而父亲大概是因为内心压抑许久,他没有去阻止自己的孩子动手。可妈妈很是生气,拆了父亲亲手为小雷做的双截棍,甩下一句我再也不管你们了。如果可以活得轻松一些,我也不愿这么挣扎,这大概是妈妈心中所想。她在别人眼中是“郭老师”,可她最怕的一句话一定是“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她怕自己的儿子长大后像她,像她的丈夫一样没有出息。她很疲惫,疲惫于自己在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色,这是每一个母亲,每一个普通家庭中女人的艰难。
“你为什么想去三中?”饭后的餐桌小雷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回家的路上一家三口美滋滋的,小雷坐在父亲的自行车上很是开心,父母一脸轻松,妈妈又问了一遍小雷这个问题。“因为三中的校服最帅,还配一根三哥那样的皮带。”顿时,父亲停下自行车,丢下小雷一个人骑得飞快走了。一开始我没有想到在这里怒气冲冲的居然是一向对儿子好脾气的父亲,后来我想他一定是对自己的儿子很失望。可那只是小孩子单纯的崇拜,他并不知道父母得因此付出多大的代价,他并不懂他的苦是有人替他受着,有人替他负重前行。孩子如此,也是大多数普通阶层父母的悲哀,从一开始他们便用了错误的教育方式。在我看来,不是说孩子需要多成熟懂事承担什么家庭重担,但孩子应有知情的权利,有他自己的选择与判断并为之付出一定的责任与代价。
坐在田间小雷和父亲面对面吃东西。小雷没头没脑的冒出一句:“爸我不去三中了。”小雷不知道他这一句话并不能挽回什么局面。也许是母亲一句“你这一分是我和你爸一个月的工资呢”触动了他,于是小孩子单纯的以为自己该懂些事,作出了自己极大的的牺牲,可现实多无奈啊。父亲拍了拍小雷的头。回家的路上楼上的老头又像电影开场时唱“天下兴亡多少事 茫茫我神州”。是的,歌还是这首歌,可多少事变了。但小雷小小年纪,需要懂天下兴亡吗?他都不懂得父母亲戚为他的付出,他甚至不知道爸爸快要离开家了。
“他妈的你小子想跟我作对啊”这一幕电影开场一家人在看的电视,中场再出现时台词重复了三遍。剧中剧里人与人作对,剧里现实与人作对。父亲拿出磁带,疯了一般的撕扯,是深感生活的无力,如同剧中剧里卡顿的画面,不得向前。小雷听到客厅的响动,偷偷打开房门探出头来,看到父亲正在打拳。旁人看来笨拙还有些可笑不成章法的拳脚,是父亲自以为的能力,无处发泄。我们赤手空拳来到人世间,不顾一切,仍然没有改变什么,包括自己。
为父亲饯行的前一晚大家有些争执。是真的满怀抱负不屑于苟且还是空有理想的一群人的自我安慰呢?妈妈的话,想要的踏实,许多母亲的影子。前阵子网易云大火的《我想和你吃个饭》歌词里没有车没有房,还对未来迷茫还想去流浪。空有理想和热血可不够啊,等我挣大钱的时候,会跟这样的你在一起,牵手转一转,但一无所有的话,怕是两个人都会饿死。但歌舞厅那一幕唤醒了我心中莫名的热情。“明天去航行,亲人的蓝头巾,将在船尾飘扬”歌声中,像是对未来有了热血沸腾的期待,大家都在自顾自的热闹,父母牵手跳舞,这个时候小雷穿着他期待的那套三中校服,趴在桌上,沉沉睡去。
临行前夜,父亲拿着那根“像三哥一样帅气的”皮带走到房间看看儿子,叹一口气离开。我想起自己离家的前一晚,也会失眠。第二天清早,父母提着行李,牵着睡眼惺忪的小雷一路小跑赶大巴车。整个场景文艺又现实,大巴车催人快走,离开得很迅速,小雷没有像一般的电影里演的那样追着车跑,只是蹙眉看着远方,像失去了什么一样,一丝空洞一分茫然一副似懂非懂的样子。似乎年少时我也经历过这一幕,眼神和小雷是一样的。父亲没有挥手示意离别,甚至来不及转头再向窗外看一眼,车没有等人好好说再见。可在车上听到“就在那个下雨的星期天 我送你离开故乡……你在他乡还好吗 是否想过靠我的双肩”这首歌时,他流泪了。
父亲走后的大家庭里,长年卧病在床的小雷太姥去世了。整个家庭的关系也有所缓和,“妈,过去是我不对,您要不哭吧,不哭出来难受”。一双手搭在另一双手上,眼泪流下的那一刻,是与往事和解,与自己和解。大合影里小雷挥起了手臂,唯独少了父亲,小雷也从坐爸爸的自行车变成了自己推着自行车,穿着校服走在路上。家里床头是父子的合影,床上是父亲亲手做的双截棍。另外,三哥的父亲去世,他仿佛一夜长大。钙奶饼干,剧组发的夜宵,也没舍得吃,都留给了三哥。三哥对一旁安慰他的小雷吼了一声滚,与之前和人一起勒索他人的零花钱不同,那时的一声“滚”是不屑和目中无人,这一刻是硬撑,不想让小孩子看到他无助、需要依靠的样子。夜晚小雷家的昙花开了,一切在悄悄改变了。
电影最后一幕是父亲在外边拍片的样子,画面转为了彩色。也许农村的世界是黑白,而外面是彩色。看样子父亲在外头过得还好,算是令人慰藉的结局。昙花开放,大概意味着八月里夏天的燥热不安过去了,而快要到来的秋天,是成熟稳重,生活趋于平静。
整部片子的细节处理得很好,小雷家房间门上贴着崔健《一无所有》的海报(这是第二让我震撼的部分,关于崔健在那个年代的影响力不必多说,也许在电影中也有着一定的寓意),父亲离开家前一夜大家相聚时“我抽万宝路”的台词,临近电影结束墙上的“乐队”二字,都深刻的体现了那就是九十年代所具有的样子。唯一我觉得缺憾的是一个极小的部分,或许导演都未曾注意——有一幕父亲骑自行车载小雷回家时,巷中一群人跳舞。广场舞的音乐是用了卓依婷的《东南西北风》,而这首歌2000年才发行,并不是九十年代初。
片尾曲《青青的野葡萄》歌词是顾城的诗《安慰》,也是一部1985年老电影里的歌。电影院人不多,但大都都没有先走,而是静静看到了最后一秒,我忽然想起去年声名大噪的《路边野餐》。不同的是,《路边野餐》有刻意的文艺,穿插晦涩的诗歌,而《八月》是没有丝毫华丽词藻的老故事,是陈旧的老照片。回去的路上看了电影之前的海报宣传——留住好时光。可我并不觉得好时光需要去留住,我认为,好时光应该在未来,过去的,就妥帖收藏小心安放。
玛格丽特·米歇尔那本著名的《飘》,英文书名是《Gone with wind》,随风而去;《八月》翻译成The summer is gone,夏天走了。某方面,电影与书是一样的,所记录过都是逝去的生活。No matter how,our life is gone.
The Summer is Gone——八月,是七月流火。
2017.03.26
小葱
但“八月”二字出现的时候,电影的英文翻译便给了我一个极大的震撼,The summer is gone,不是简单直接的August,而是婉转的表达——夏天走了。那一刻我意识到它可能是跟我往常所看的文艺片是不一样的,并不只适用于无聊的消遣,于是决定认真观摩解读,好好写一篇影评。
故事背景是在九十年代初的西部小城,国家开始实施国企改革,铁饭碗被打破,国有制片厂家属院里,每一个简单家庭的生活都被改革所影响,而十一岁的小雷就这样在经济变革与家庭改变之间懵懂成长。电影里每一个人物都有鲜明的个性,都是一个时代的体现,比如小雷,比如父母和一群亲戚,比如看似无关紧要的地痞三哥。
虽说这是一部致敬父辈的电影,但几十年来,许多景象还是日复一日从未变过。大爷大妈们在嘈杂的环境下打牌,四周不乏一些围观的人,小孩儿穿着廉价的衣服凉鞋在旁边跳橡皮筋,大人喊小孩儿回家吃晚饭时男孩一脸不情愿的说“我想多玩会儿”。小雷的童年也是我的童年,准确的说,是我小时候生活在乡下时眼里看到的童年,不是经历的童年。我充斥在弹琴画画练字背单词中的童年并不快乐。
也许是喜欢孩子的缘故,一直觉得孔维一——就是剧中的张小雷小朋友,他笑起来真好看,当他看着妈妈用古怪的方式浇花,“噗嗤”一声就笑了,那是小孩子才有的调皮捣蛋古灵精怪的笑,连带着看电影的我都发自内心的笑了。许多人围在河边看三哥在羊肚子里取出菩提子(并不确定三哥是在干什么,凭直觉所想),一群大人里面,只有小雷的眼神带着孩子才有的好奇、探究。大人都是沉闷死气的,只有孩子为生活的枯燥带来了生机。
家属院里运动会拔河,还未分出胜负时,厂子里的车动不了了,大家都去推车,直到车子都发动了许多人还是跟着跑,大喇叭里念着热血沸腾的诗仿佛这是一场闹剧。随着人群渐远,镜头聚焦到小雷身上,小雷的神情一半茫然一半似乎又懂得了些什么,半知半解的眼神,瘦瘦小小的身影,这样孩子气对未知的不解,总让人想越过面前的屏幕去抱一抱他。小雷挥动着手里的双截棍,咚咚响的跑到楼上尽头的房间,偷偷的打开门,又忍不住问“爸爸,这是什么?”“放电影。”“你为什么不去参加运动会?”爸爸当然不会回答,跟小孩子怎么解释得清楚,再说就算回答,又能回答出什么。他剪了一截胶片给小雷,孩子终归是孩子,马上拿到窗边把玩,问父亲“这是谁呀?”“这是你老云叔叔。”这一刻父子俩的场面格外温馨,窗外通过胶片透进来的光,仿佛是父子俩的希望。
父亲张晨一直像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不要低下高贵的头颅”——这恐怕是不需要考虑生存的艰难不识愁滋味的少年才有资格说出的话,冲动的意气用事的父亲,喝醉酒的父亲,不愿向现实妥协的父亲,带小雷看电影时流泪的父亲,多像个文艺莽撞的大孩子。不要说是一个父亲的年龄,就连现在的我们,逐渐成长麻木,操劳担心过不去的现在和未来,已然很少在别人的故事里流自己的泪了。
电影中场,小雷开始由小孩转变为少年了。学校主任一回头看到小雷,“这谁家的小孩儿?”“咋呀”——少年身上独有的戾气。还有后来父亲与小雷没有看成的那场电影,有钱人的倨傲和他儿子胖小子眼里的轻蔑,瘦弱的小雷脸上再也藏不住愤怒,他的手和身体已经做出了最直接的反应。而父亲大概是因为内心压抑许久,他没有去阻止自己的孩子动手。可妈妈很是生气,拆了父亲亲手为小雷做的双截棍,甩下一句我再也不管你们了。如果可以活得轻松一些,我也不愿这么挣扎,这大概是妈妈心中所想。她在别人眼中是“郭老师”,可她最怕的一句话一定是“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她怕自己的儿子长大后像她,像她的丈夫一样没有出息。她很疲惫,疲惫于自己在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色,这是每一个母亲,每一个普通家庭中女人的艰难。
“你为什么想去三中?”饭后的餐桌小雷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回家的路上一家三口美滋滋的,小雷坐在父亲的自行车上很是开心,父母一脸轻松,妈妈又问了一遍小雷这个问题。“因为三中的校服最帅,还配一根三哥那样的皮带。”顿时,父亲停下自行车,丢下小雷一个人骑得飞快走了。一开始我没有想到在这里怒气冲冲的居然是一向对儿子好脾气的父亲,后来我想他一定是对自己的儿子很失望。可那只是小孩子单纯的崇拜,他并不知道父母得因此付出多大的代价,他并不懂他的苦是有人替他受着,有人替他负重前行。孩子如此,也是大多数普通阶层父母的悲哀,从一开始他们便用了错误的教育方式。在我看来,不是说孩子需要多成熟懂事承担什么家庭重担,但孩子应有知情的权利,有他自己的选择与判断并为之付出一定的责任与代价。
坐在田间小雷和父亲面对面吃东西。小雷没头没脑的冒出一句:“爸我不去三中了。”小雷不知道他这一句话并不能挽回什么局面。也许是母亲一句“你这一分是我和你爸一个月的工资呢”触动了他,于是小孩子单纯的以为自己该懂些事,作出了自己极大的的牺牲,可现实多无奈啊。父亲拍了拍小雷的头。回家的路上楼上的老头又像电影开场时唱“天下兴亡多少事 茫茫我神州”。是的,歌还是这首歌,可多少事变了。但小雷小小年纪,需要懂天下兴亡吗?他都不懂得父母亲戚为他的付出,他甚至不知道爸爸快要离开家了。
“他妈的你小子想跟我作对啊”这一幕电影开场一家人在看的电视,中场再出现时台词重复了三遍。剧中剧里人与人作对,剧里现实与人作对。父亲拿出磁带,疯了一般的撕扯,是深感生活的无力,如同剧中剧里卡顿的画面,不得向前。小雷听到客厅的响动,偷偷打开房门探出头来,看到父亲正在打拳。旁人看来笨拙还有些可笑不成章法的拳脚,是父亲自以为的能力,无处发泄。我们赤手空拳来到人世间,不顾一切,仍然没有改变什么,包括自己。
为父亲饯行的前一晚大家有些争执。是真的满怀抱负不屑于苟且还是空有理想的一群人的自我安慰呢?妈妈的话,想要的踏实,许多母亲的影子。前阵子网易云大火的《我想和你吃个饭》歌词里没有车没有房,还对未来迷茫还想去流浪。空有理想和热血可不够啊,等我挣大钱的时候,会跟这样的你在一起,牵手转一转,但一无所有的话,怕是两个人都会饿死。但歌舞厅那一幕唤醒了我心中莫名的热情。“明天去航行,亲人的蓝头巾,将在船尾飘扬”歌声中,像是对未来有了热血沸腾的期待,大家都在自顾自的热闹,父母牵手跳舞,这个时候小雷穿着他期待的那套三中校服,趴在桌上,沉沉睡去。
临行前夜,父亲拿着那根“像三哥一样帅气的”皮带走到房间看看儿子,叹一口气离开。我想起自己离家的前一晚,也会失眠。第二天清早,父母提着行李,牵着睡眼惺忪的小雷一路小跑赶大巴车。整个场景文艺又现实,大巴车催人快走,离开得很迅速,小雷没有像一般的电影里演的那样追着车跑,只是蹙眉看着远方,像失去了什么一样,一丝空洞一分茫然一副似懂非懂的样子。似乎年少时我也经历过这一幕,眼神和小雷是一样的。父亲没有挥手示意离别,甚至来不及转头再向窗外看一眼,车没有等人好好说再见。可在车上听到“就在那个下雨的星期天 我送你离开故乡……你在他乡还好吗 是否想过靠我的双肩”这首歌时,他流泪了。
父亲走后的大家庭里,长年卧病在床的小雷太姥去世了。整个家庭的关系也有所缓和,“妈,过去是我不对,您要不哭吧,不哭出来难受”。一双手搭在另一双手上,眼泪流下的那一刻,是与往事和解,与自己和解。大合影里小雷挥起了手臂,唯独少了父亲,小雷也从坐爸爸的自行车变成了自己推着自行车,穿着校服走在路上。家里床头是父子的合影,床上是父亲亲手做的双截棍。另外,三哥的父亲去世,他仿佛一夜长大。钙奶饼干,剧组发的夜宵,也没舍得吃,都留给了三哥。三哥对一旁安慰他的小雷吼了一声滚,与之前和人一起勒索他人的零花钱不同,那时的一声“滚”是不屑和目中无人,这一刻是硬撑,不想让小孩子看到他无助、需要依靠的样子。夜晚小雷家的昙花开了,一切在悄悄改变了。
电影最后一幕是父亲在外边拍片的样子,画面转为了彩色。也许农村的世界是黑白,而外面是彩色。看样子父亲在外头过得还好,算是令人慰藉的结局。昙花开放,大概意味着八月里夏天的燥热不安过去了,而快要到来的秋天,是成熟稳重,生活趋于平静。
整部片子的细节处理得很好,小雷家房间门上贴着崔健《一无所有》的海报(这是第二让我震撼的部分,关于崔健在那个年代的影响力不必多说,也许在电影中也有着一定的寓意),父亲离开家前一夜大家相聚时“我抽万宝路”的台词,临近电影结束墙上的“乐队”二字,都深刻的体现了那就是九十年代所具有的样子。唯一我觉得缺憾的是一个极小的部分,或许导演都未曾注意——有一幕父亲骑自行车载小雷回家时,巷中一群人跳舞。广场舞的音乐是用了卓依婷的《东南西北风》,而这首歌2000年才发行,并不是九十年代初。
片尾曲《青青的野葡萄》歌词是顾城的诗《安慰》,也是一部1985年老电影里的歌。电影院人不多,但大都都没有先走,而是静静看到了最后一秒,我忽然想起去年声名大噪的《路边野餐》。不同的是,《路边野餐》有刻意的文艺,穿插晦涩的诗歌,而《八月》是没有丝毫华丽词藻的老故事,是陈旧的老照片。回去的路上看了电影之前的海报宣传——留住好时光。可我并不觉得好时光需要去留住,我认为,好时光应该在未来,过去的,就妥帖收藏小心安放。
玛格丽特·米歇尔那本著名的《飘》,英文书名是《Gone with wind》,随风而去;《八月》翻译成The summer is gone,夏天走了。某方面,电影与书是一样的,所记录过都是逝去的生活。No matter how,our life is gone.
The Summer is Gone——八月,是七月流火。
2017.03.26
小葱